2019-08-18 07:57:28
1. 文学是一种表达方式
——与北村对话
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喜欢北村。有一段时间因无法了解他的情况竟然还比较焦虑。北村应该算一个异数。他与苏童、余华、格非这些同龄作家有着很大的不同。
北村现在似乎是一个行走一类的人。用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在路上。他的手机号总是不确定。他可能在福州,也可能在北京。
在我与北村对话时,北村经常提到“他”,譬如说,“那是因为他给出了亮光”。我开始不明他所说的“他”所指为谁,那种亲切的语气让我迷惘。后来终于知道“他”其实就是北村心中的神与上帝。我不便指明,但我体会到北村对“他”的那种亲密与靠近。北村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北村对自己能够达到某种高度充满了信心。
1992年前后信仰背景的变化可能造成了他的创作的变异。好在,北村的光还是在的。而我们知道,光是上帝的语言,北村让光说话。

北村与光直接发生联系除了他的基督以外,还有影视。很多人有着共同的疑问:北村有没有被影视拐跑?姜广平同志觉得差不多了,北村认为,不,我是在以影视养文学。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北村有道理,因为福克纳也写过一些非常蹩脚的电影脚本。
在我看来,北村完成了这样一个转变:先锋,圣徒,接着是隐于影视的隐士。我们说,北村就像他自己所讲的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有的问题他尝试着解决,但有些问题他就放在那里,不是为了解决的问题,而是为了思考的问题。
北村是一个行走着的人。他一直走在他的内心里。
忘了告诉你,北村原名叫康洪。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及了。
2. 我抓住了两个世界
——与红柯对话
他的原名叫杨宏科。然而,一旦叫做红柯,便有了无限的诗意。
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排斥红柯。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末。
那时我觉得红柯的写作不体面,或者用现在非常流行的话讲,红柯在引领我们走进一个陌生的语境。我们说什么也无法在他的引领下进入新疆。我到现在还记得,我在苏北乡一家中学的食堂二楼住着的时候,读到了他的《美丽奴羊》,但我真的没有读下去。
我硬着头皮开始阅读红柯是在打算与他做对话之前。一挤进去才发现,红柯将新疆写得活灵活现。在红柯的笔下,新疆是热烈的,在红柯的笔下,新疆有两个世界。“我抓住了两个世界”,这句出自《金色的阿尔泰》里的话,我一见钟情,后来一用再用。
还需要说明一点的是,阅读红柯在我的阅读史上是一次革命。说实在的,我以前很少关注像阎连科、红柯这样的作家。从与红柯对话开始,我开始潜心阅读并沉下心来接受一些作家。
说到对红柯的阅读,我不得不提到一个我非常尊敬的作家,他就是毕飞宇。有好些次,我与他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说到红柯,他总是非常坚定地说,他写得不错,而且写得很疯。你看看,相当不错的一个作家。读过之后才发现,是的,红柯了不起,一个相当了不起的作家。
这就让我想到了另一点,当代的作家,如刁斗所言,已经终生在为文学奉献着,其文学精神与文学思想已经远远超过了前一代的大师们了。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浮躁,使得人们忽略了这道美丽的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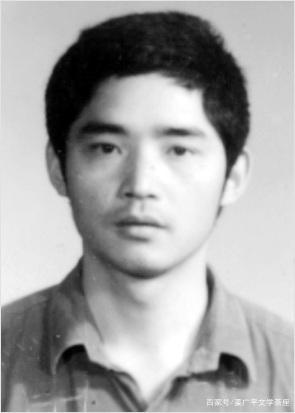
6.“文革”记忆与土地情怀
——与阎连科对话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阎连科。从精神上讲,我常常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他像我精神上的长兄。他的作品,时时让我回首我自己走过的岁月。《情感狱》里的“瑶沟”系列是能让人看见一代人的影子的。
阎连科无疑是非常优秀的。像这样一位作家,是无法圈定在哪一种流派里让人为他作一个确切的定位的。他的军旅题材的小说让人觉出理性的深度和力量,他的乡土题材的小说让人觉出他的深情与执著。有时候他举重若轻,有时候他举轻若重。像《兵洞》,我觉得它属于前者,《寂寞之舞》与《朝着东南走》便属于后者。评论家李敬泽说连科扛千斤之鼎,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比方。
但这只是一个现成的比喻。真正的打鼎之作当然是《日光流年》与《坚硬如水》。前面一本书,用了作家四年的时间写成,评论家王一川认为可以问鼎诺贝尔奖。我认为也完全可以——至少以2000年的标准是可以的。连科的写作到这两部作品时,已是一条宏阔的大河,气象万千,森然警人。
连科的本意是在寻找。可能很多人是从这个意义上定位他是乡土派作家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人世之间,我们离社会很近,但离家太远,离土地太远。我们已经出行了这么多年,把不该忘记的都给忘了;或者说,我自己一来到这个世上,从未来得及用心去思考这些,就已被匆匆地裹进了熙攘的人流,慌慌张张地上路走了。”他觉得必须帮助自己找到一些人生的原初意义。
这大概就是连科为什么在自己的简介里什么都不回避的原因。说得那么率真,那么诚恳。
现在再来听听他说得更详细的。

7.我希望走向开阔
——与李修文对话
在与我对话过的诸多作家中,李修文是最年轻的。
与李修文对话是有难度的,因为李修文作品的量不是很多。在与我做对话时,李修文才只有一部长篇,那就是《滴泪痣》。他寄给我的也只有一本,那就是《心都碎了》,是一本中短篇小说集。
李修文是一个文学天才。也许这样的话还是有点过,但是,到过一次日本便能写出《滴泪痣》这样的作品来,实在令人称道。他是一个特别关注细节的作家,也因此,对日本作家那种在精细与细节上进行打造的文学行为特别感动。他在《莽原》上曾经发表过一篇创作札记《楼上的官人们都醉了》,这样的文字也许是激起我与他的对话的直接动因。
我接触李修文是上个世纪90年代读《作家》杂志时开始的。我发现,是细节的力量,召唤着这个作家的改变。他会一方面力图破坏,一方面又力图将爱情写得古典、纯粹、灿烂。写花木兰也好,写李清照也好,包括写林黛玉也好,我们见到了爱情世俗的一面,但到了《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时,情形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爱情越来越直奔它的主题:死亡。李修文越来越明晰地建立了自己的爱与死的文学帝国。
当然,对小说《滴泪痣》,《挪威的森林》的翻译者林少华称“这里边既有爱的刻骨铭心,又有爱的无可救药……不管怎么说,这种极端在中国小说中大约是不易觅得的。”自此李修文的小说被誉为有着浓厚村上村树韵味。
但我却不希望李修文仅仅是中国的村上村树。复制或模仿永远不能成为自己。
然而,我要说一声抱歉的是,在与李修文对话的时候,还没有读到他的《捆绑上天堂》。对话结束后,他的这本书《收获》增刊上出来了。我在杭州汽车站读到了这篇长篇小说,随后给李修文拨去了电话,祝贺他的新作问世。

8.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
——与苏童对话
可能,在先锋作家中,苏童背负着的负担最重。这种负担里面还有着读者对他的那种近乎无理的期望——你是苏童,你就应该不停地写出好东西。
我真正地对先锋文学给予全面关注是在读了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之后。一家乡村中学的图书馆,很多书无法觅着,却赫然有一本这样全面论述先锋文学的书。一看,才知道出了大事儿,文坛上春秋战国时期到了。乡下人可怜,对这一切竟然一无所知。只知道有一个叫苏童的人,听说是以苏州的儿童为意象取的名字,还与巩俐有联系。巩俐出名,就是因为他有一篇叫《妻妾成群》的小说。
苏童很遥远。这是我在苏北乡下教书时的感觉。他躲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银幕之后,大男孩一般灿烂地对你笑着。但苏童告诉我,那不是苏童。那只是电影。
在1994年的那个秋季及此后漫长的时间里,我都觉得苏童没有讲话。甚至1996年,在《收获》以每期都刊发苏童一个或两个短篇的策划也似乎没有唤回人们对苏童的关注。人们头脑里的苏童还是电影后的那个苏童。难怪苏童说,他一直生活在误解中。他为此不无痛苦地对我说了一句,有谁去关注一个作家写了什么短篇呢?实际上,苏童在短篇小说的后面,而不是在电影的后面,而且恰恰是一个短篇高手。
所以,对苏童沉寂之说,苏童并不认帐。我也不认帐。所以,我要看一看苏童是如何留神听着这个世界的动静的。
苏童是丰富的。但我也要说我的遗憾。这篇对话,我们没有涉及他的长篇《米》与《紫檀木球》。《米》我没有读过,所以就不敢说。这是我评论的原则。《紫檀木球》苏童不愿说,所以也就不论。这也符合我访谈的原则。作家自己不愿说的东西,我们为什么偏要去说呢?
【注】文中图片有意打乱,请你一一分辨出是哪些名作家。谢谢!